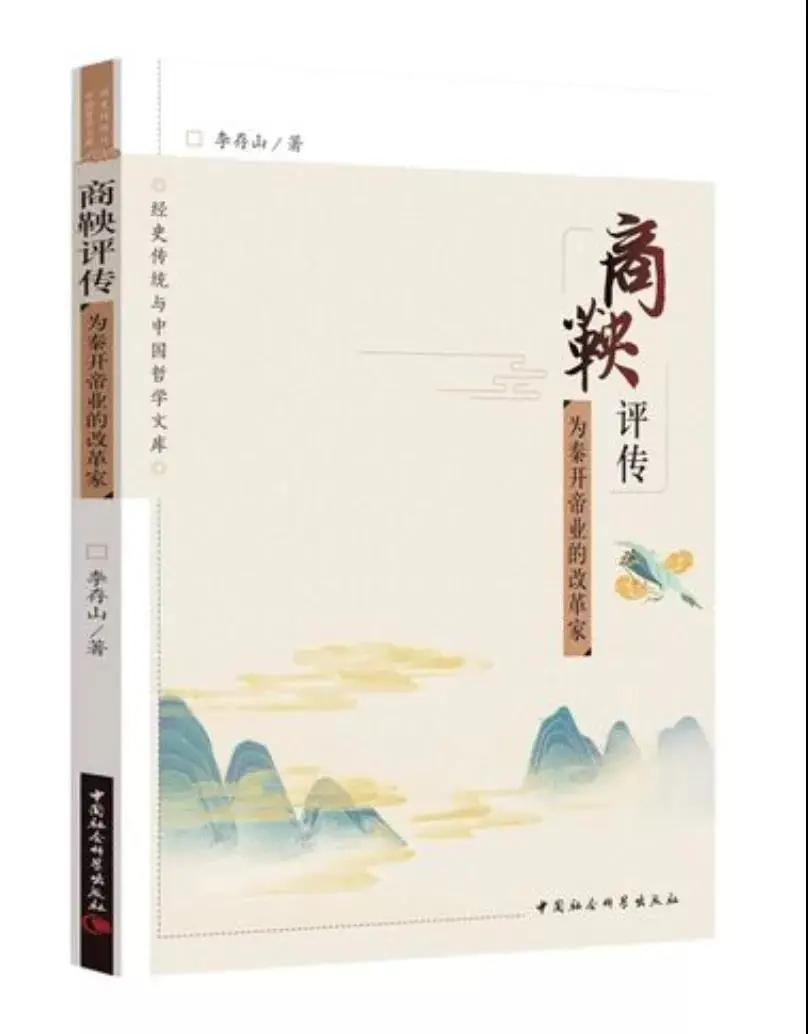
商鞅評傳
李存山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本書對商鞅變法改革和《商君書》思想進行綜合性研究。商鞅是戰國中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他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國兩次變法,力主“耕戰”“富國強兵”,使秦國迅速崛起,為后來的“秦王掃六合”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商鞅是“為秦開帝業的改革家”,其改革對后世影響深遠。而現傳《商君書》是商鞅及其后學撰寫的著作,可視為商鞅學派的思想總集。商鞅學派雖不必為秦朝速亡直接負責,但他們專制、狹隘的功利主義文化政策和對精神文明、倫理道德的忽視,亦是秦亡的原因之一。本書結合商鞅變法史實與典籍思想,不僅細致勾勒出商鞅學派的思想內容,深刻指出商鞅變法的歷史意義,同時徹底反思了商鞅學派與秦二世而亡的關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商鞅評傳》再版前言
李存山 | 文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國學熱”中,學術界的幾位著名學者與廣西教育出版社合作組織出版了一套“中華歷史文化名人評傳”叢書,當時分配我撰寫“改革家系列”的《商鞅評傳》。我對此并無準備,而且我對法家思想基本上持批判的態度。不過,我倒是愿意就此清理一下我思想中對儒法關系的認識。
我初識“商鞅”這個名字,是在文革的“批林批孔”或“評法批儒”時期,那時我曾參加過一次這方面的“學習班”,后來仍留下印象的是“商鞅車裂而死”等等。在我參加1977年高考而進入北大哲學系學習后,以前的那段經歷就都作為蹉跎歲月的“陳跡”而任其遺忘了。但是學習哲學史,特別是考上中國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后,商鞅、韓非等法家人物的思想作為哲學史上的一個思想環節而要有所認識,當然這遠非學習的重點。大約在1987年,我偶讀了商務印書館新出版的馬基雅維里著《君主論》,這本書的思想使我很容易聯想到中國的韓非子,于是就寫了一篇《馬基雅維里與韓非子》[①]。《君主論》在中國曾被譯為《霸論》,它的思想與法家思想相通,應是學術界很早就有的認識。馬基雅維里宣揚君主應當同時效法“狐貍”與“獅子”,這與韓非子的“法、術、勢”結合的思想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馬基雅維里思想的一大特點是使政治學脫離了道德,在這一點上韓非子當然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兩人所不同的是,馬基雅維里生活在15至16世紀的歐洲,而韓非子則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中國,由此而帶來對兩人懸殊不同的評價:馬基雅維里被認為是西方近代使政治學掙脫中世紀神學的束縛而與道德徹底分家的奠基者,而韓非子則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建立君主集權制度并將其與君主的權謀、權術相結合的集大成者。這實際上正反映了中西歷史發展不同的特殊性:西方歷史從古希臘羅馬進入中世紀是以基督教的統治為其特征,而中國歷史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戰亂實現國家的統一是以君主集權為其制度的保障。與此相連帶的是:西方文化的近代轉型首先是表現為掙脫基督教統治的束縛,而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則需要逐漸從君主集權制度中解放出來。如果因為馬基雅維里與韓非子都主張君主集權,也都主張政治與道德分家,就認為中國文化在兩千年之前就已進入了近代,那就太無視中西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了。
我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而開始了對商鞅、《商君書》和商鞅學派思想的研究。商鞅的生卒年(約公元前390一前338年)比韓非子的生卒年(約公元前280--前233年)早一百余年,這一百余年正是從戰國中期的商鞅變法而秦國崛起到戰國末期的強秦以其“虎狼之師”而即將完成統一“帝業”的過程。漢代的王充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這是對那段歷史的一個客觀評價。關于法家人物的著作,《漢書·藝文志》以李悝所作“《李子》三十二篇”為首,其后便是“《商君》二十九篇”。李悝的著作早已失傳,從傳世的史書記載看,他曾在任魏文侯相期間推行新政,主要是“作盡地力之教”,實行平衡糧價的“平糴”法,并著有《法經》(也早佚),他確實可作為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先驅。而商鞅則是繼承了李悝、吳起之“遺教”,在《法經》的基礎上制定了《秦律》,把“重農”與“強兵”密切結合起來,在秦國實行了兩次變法,乃致“秦人富強”,商鞅實為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真正開創者。韓非子說“秦行商君法而富強”,“此臣之所師也”(《韓非子·和氏》),但他批評商鞅“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主無術于上之患也”(《韓非子·定法》),又說“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韓非子·人主》),“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他之所以被稱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因為他在商鞅重法的基礎上又綜合了君主的權術和權勢的思想。
商鞅變法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本書的第一至五章已對商鞅兩次變法的內容和成效,及其前后背景和“商君雖死,秦法未敗”的結局,作了較詳細的論述。第六章說明《商君書》在戰國中后期已普遍流傳,對秦國政治影響深遠,《商君書》中傳世的二十六篇有商鞅所自撰和疑為自撰的,也有商鞅后學所作的,《商君書》可視為以商鞅為首的商鞅學派思想的總集。第七至十二章則分別對商鞅學派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和文化思想展開論述,并最終從“制度與文化”的角度評價商鞅學派的歷史功過,討論儒法的沖突與合流,以及對現代人的幾點啟示。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是嚴格按照“中華歷史文化名人評傳”叢書的要求,對傳主的歷史事實不作“子虛烏有的夸張演義”,而是“本著科學、嚴謹的學術態度,對傳主的活動作盡量生動活潑的敘述”,“雖然各位傳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冊,但卻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表現出歷史和個人的局限,甚至不無糟粕”,因此對他們的評價也要采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應該說,這樣的要求至今仍是正確的。這次本書再版之際,我將此書重讀一遍,因書中的論述都是以史料為依據的,所以對這本二十多年前的舊著只作了個別文字的修改,而保留了舊版的原貌。但這畢竟是二十多年前寫的,所以我也借這次再版之機略談幾個問題。
關于“商鞅三試秦孝公”,即商鞅先后向秦孝公說以“帝道”“王道”和“霸道”,最終是以“霸道”而君臣契合。歷史上對此有不同的議論,本書沒有一一評說,而權以嚴萬里的“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以申其任法之說”作結。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語》的記載中并沒有關于“帝道”和“王道”的明確劃分,而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簡《唐虞之道》中卻有“唐虞之道,禪而不傳”的思想,尤其是此篇說“不禪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這就指出了若想“化民”只能實行禪讓而不能世襲。后來發布的上海博物館藏《容成氏》和《子羔》兩篇,具有與《唐虞之道》同樣的思想傾向(如《子羔》開篇說“昔者而弗世也,善與善相授也,故能治天下,平萬邦”,“弗世”即不是父子相傳)。郭店竹簡和上博館藏竹簡都屬于戰國中前期的文獻,也就是“孔孟之間”、顧炎武所謂“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的那個時期的文獻。應該說在戰國中前期,曾經流行過崇尚禪讓而反對世襲的一種思潮。與此相應的是,在《商君書·修權》篇有“論賢舉能而傳焉”的禪讓思想,在《戰國策·秦策一》也有秦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的記載,在《呂氏春秋·不屈》篇也有“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愿得傳國。’惠子辭”的記載。商鞅、惠施都是戰國中期的人物,那時已是禪讓思潮的末流,在君主的絕對權勢之下他們不敢接受禪讓也是當然的。最終結束這一思潮的是公元前318年在燕國發生的“讓國”悲劇事件,孟子曾親臨此事,應是鑒于這個事件的悲劇性質,說明禪讓在當時的情勢下已無現實的可能,所以孟子在回答“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有諸”時,才說“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孟子·萬章上》),也就是把“禪而不傳”改成了“禪”與“傳”兩可[②]。
如果明白了上述背景,那么商鞅分別以“帝道”和“王道”試探秦孝公,可能就不是“假迂遠悠謬之說”來試探,而是以堯舜禪讓為“帝道”,以世襲而實行德政為“王道”。從儒家方面說,就可以看出儒家對于政治制度的主張是可以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作調整的:在燕國的“讓國”事件之前,儒家曾一度有“禪而不傳”(欲“化民”就只能禪讓而不能傳子)的思想;在燕國的“讓國”事件之后,孟子將其調整為“禪”與“傳”兩可。
商鞅最終是以“霸道”而達到了君臣契合,這說明秦國最終以“霸道”完成統一“帝業”,不僅是商鞅個人的主觀思想作為,而更是被戰國時期的客觀形勢,特別是戰國時期的君主制度所決定的。當時結束分裂戰亂而實現國家的統一已經是時代的大勢所趨,而儒、法兩家在如何實現統一的問題上分別提出了兩條路線,一條是商鞅變法的“霸道”,另一條是孟子提出的“仁政”“王道”。孟子的“仁政”“王道”之說體現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而當時的梁惠王、齊宣王認為這是“迂遠而闊于事情”,因此,孟子的“仁政”“王道”之說在當時行不通,這也是被戰國時期的客觀形勢,特別是當時的君主制度所決定的。孟子曾肯定齊宣王懷抱著“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設想以“仁政”“王道”的方式可以實現這種“大欲”,但實際上就像秦孝公不能接受商鞅所試探的“帝道”“王道”一樣,梁惠王、齊宣王等等也是不能接受孟子的“仁政”“王道”之說的,這主要是被當時的君主制度所決定的。
關于如何評價主要由法家學說建立的君主集權制度,這應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形勢和“通古今之變”的兩個角度來予以評價。戰國時期的分裂戰亂、兼并戰爭是十分殘酷的,孟子就已指出當時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孟子·公孫丑上》),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希望以此而“天下定于一”。但是中國歷史最終是選擇了以法家學說的“霸道”,即以“農戰”的經濟實力和軍事暴力來統一天下,這就加劇了戰國時期兼并戰爭的殘酷性,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在商鞅變法之后,秦國已經成為一部“農戰”的機器,“故圣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商君書·算地》),“圣王見王之致于兵也,故舉國而責之于兵……能使民樂戰者王”(《商君書·畫策》),在“壹教”“刑賞”的驅迫下,秦民也陷入戰爭的狂熱,“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商君書·賞刑》),“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也”(《商君書·畫策》),秦國成為以重農為基礎而一切為了戰爭的軍國主義國家。因此,就秦國實現統一“帝業”的手段來說,是應受到譴責的。但是秦國畢竟是以“霸道”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并以君主集權的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等鞏固了國家的統一,而且“漢承秦制”,這也被漢以后的歷代王朝所繼承,這從歷史的發展來說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在漢初的郡縣制與封建制之爭中,賈誼最先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新書·藩強》),即漢王朝所推行的“強干弱枝”政策,這說明漢初的儒家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免于分裂和戰亂,采取了鞏固君主集權、擁護郡縣制而反對封建制的立場。在此之后,唐代的柳宗元著有《封建論》,較為充分地論述了從封建制到郡縣制的歷史必然性。而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則從另一視角說:“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讀通鑒論》卷一)所謂“大公”就是說郡縣制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從而也有利于人民的生產與生活。但是,君主集權畢竟有其體制上的弊病,雖然漢代開始的尊儒延長了一個王朝治亂興衰的周期,但歷代王朝終不免落入始興終亡的“宿命”,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給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特別是宋代以后,君主集權更向極端發展,而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又給士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故而王夫之說:“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黃書·古儀》)“圣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延。”(《黃書·宰制》)對于秦以后所實行的君主集權制,我們應給予歷史的、辯證的評價,既要看到它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它在近代辛亥革命以后被民主共和制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就像劉邦曾經刑白馬立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一樣,孫中山也曾說民國建立之后“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③],這實際上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時代。
關于商鞅變法的“為田開阡陌封疆”,歷來也有不同的說法,這涉及史學界曾作為一個研究熱點的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問題。我對此不可能作專業性的研究,當時只是參酌一些史料,綜合采納了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商鞅變法“鏟除田地間原有的疆界,廢除井田制,確認土地的私人占有 ”。這仍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在云夢秦簡、青川木牘和張家山漢簡相繼出土之后,史學界對此討論頗多[④]。聯系到商鞅第一次變法的“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所謂“名田宅”即按照尊卑爵秩等級占有不同的田宅。這又與當時的“軍功授田制”相聯系,而“授田制”屬于土地國有,而非土地私有。但實際上,土地國有與土地私有在這里不宜作截然的劃分。漢代的董仲舒曾主張“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漢書·食貨志》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所謂“限民名田”即主張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數量,而“名田”即相當于商鞅變法的“名田宅”。有歷史學家指出:“受田制就是名田制”,“秦漢的受田宅制是一種有受無還的土地長期占有制度”,“土地制度有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規律,即土地一經確定為長期占有制,必然迅速演變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導致土地兼并”[⑤]。如此說來,商鞅變法的“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就是確立了按照尊卑爵秩等級“長期占有”不同的田宅,這里的“長期占有”當然是指私人長期占有。而“為田開阡陌封疆”,當就是鏟除了井田制原有的土地疆界,而按照私人長期占有和新的畝制,建立了新的田界。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記載秦昭王相蔡澤說:商鞅“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所謂“靜生民之業”,當就是明確了土地的私人長期占有。這種“有受無還的土地長期占有制”是通過國家的“受田”實現的,如果說它不是“土地私有制”,那么可以說它是由土地國有向土地私有轉化的一種形式。一般認為,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實田也”(《史記集解·秦始皇本紀》),是國家承認土地私有的一個標志,而這個標志應就是由國家承認了早已存在的土地私有的現實,這個現實是由商鞅變法開啟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漢書·食貨志》記載董仲舒說:“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這里的“古者”云云是講古井田制的情況,而說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賣買”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新出土的云夢秦簡、青川木牘中沒有“民得賣買”土地的記錄,而且當時秦國的土地私人長期占有還帶有“授田”的形式,主要是為了“靜生民之業”,以獎勵耕戰,所以當時可能還沒有發生“民得賣買”土地的情況。至于在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實田”之后是否允許民間買賣土地,似乎可以存疑。“漢承秦制”,包括繼承了秦國的土地制度,而在漢初就已發生了買賣土地的情況,如蕭何為避嫌乃“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文帝時晁錯上書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 (虐) 〔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漢書·食貨志》)隨著土地可以買賣,土地兼并也就日益加劇,到漢武帝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并興,而民去本”,于是有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而他所說的“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當主要是針對漢初以來的土地兼并情況,而在商鞅變法時“壞井田,開仟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漢書·食貨志》),彼時及至秦統一天下可能還沒有出現土地的“民得賣買”。盡管如此,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發展規律是土地一經確定為私人長期占有,“必然迅速演變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導致土地兼并”,這個規律的發端是由商鞅變法開啟的。
本書在論述商鞅變法的“為田開阡陌封疆”時,尚不了解史學界根據出土新史料討論秦漢土地制度的情況,故有些論述失于簡單化,不盡符合秦漢土地制度發展的歷史進程,這是我在本書再版時需要說明的。由此想到,在本書的其他部分,限于本人的學識,可能也有一些不當之處,尚祈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關于《商君書·開塞》篇的“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與漢初的尊儒有著思想上的聯系,這在本書中有所涉及,但沒有集中的論述。在本書完稿后,我又專寫了一篇《<商君書>與漢代尊儒》[⑥],這次本書再版順便將此文附于后,以便學界同仁參考。
[①]此文載于《讀書》雜志1987年第4期。
[②]參見拙文《反思經史關系:從“啟攻益”說起》,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③]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7頁。
[④]參見閆桂梅《近五十年來秦漢土地制度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7年第7期。
[⑤]朱紹侯:《論漢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壞》,《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⑥]此文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后來此文的英譯稿被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選入她主編的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Vol.47 No.2,2016。
《商鞅評傳》目錄
前言
第一章入秦之前
第一節童年時期的戰國形勢
第二節繼承李悝、吳起之余教
第三節公叔痤臨終薦賢
第二章變法前夕
第一節秦孝公頒布求賢令
第二節商鞅三試秦孝公
第三節改革與守舊的御前辯論
第三章第一次變法
第一節徙木賞金取信于民
第二節第一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第三節貫徹新法的斗爭和成效
第四章第二次變法
第一節遷都咸陽奠基帝業
第二節第二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第三節秦人富強收復河西
第五章商鞅雖死秦法未敗
第一節趙良的警告
第二節商鞅車裂而死
第三節秦法未敗
第六章商鞅與《商君書》
第一節《商君書》的歷史流傳
第二節《商君書》的作者
第三節《商君書》各篇的寫作時間
第七章商鞅學派的哲學思想
第一節不言鬼神和天道
第二節歷史進化論
第三節自然人性論
第八章商鞅學派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君主集權與民本主義
第二節尚力與任法
第三節厚賞重刑與重刑輕賞
第九章商鞅學派的經濟思想
第一節農為強國之本
第二節興農的政治措施
第三節興農的經濟措施
第十章商鞅學派的軍事思想
第一節兵為強國之要
第二節用兵必先立本
第三節謀略與戰法
第十一章商鞅學派的文化政策
第一節單一的意識形態
第二節《商君書》所列各種“國害”
第三節商鞅學派與“焚書坑儒”
第十二章制度與文化——代結束語
第一節商鞅學派的歷史功過
第二節儒法的沖突與合流
第三節對現代人的幾點啟示
附錄《商君書》與漢代尊儒——兼論商鞅及其學派與儒學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