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四川大學(xué)古籍所編纂的線裝版《儒藏精華》共計(jì)36函260冊,日前正式出版發(fā)行,向黨的十九大獻(xiàn)上了一份厚禮。《儒藏精華》于《儒藏》基礎(chǔ)上萃取精華而成,按照計(jì)劃,明年將完成共計(jì)600余冊《儒藏》的全部編纂與出版工作。川版《儒藏》是當(dāng)代學(xué)人在整理國故上的新貢獻(xiàn),也是對蜀學(xué)悠久治學(xué)傳統(tǒng)的繼承與接力。本文將告訴我們,世代蜀學(xué)在整理儒學(xué)文獻(xiàn)方面是如何“接著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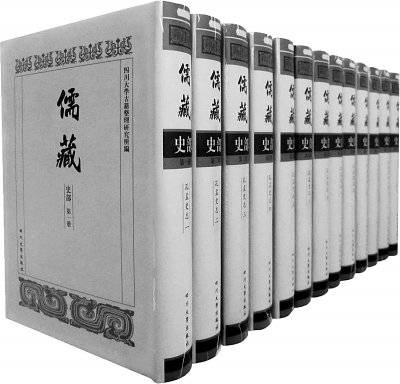
蜀學(xué)是發(fā)生在巴蜀大地,曾經(jīng)與中原學(xué)術(shù)并行發(fā)展,最終影響并融入中華學(xué)術(shù)寶庫的區(qū)域性學(xué)術(shù)。蜀學(xué)在其產(chǎn)生和演變、發(fā)展的歷程中,與儒家經(jīng)典和儒學(xué)文獻(xiàn),曾發(fā)生過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儒家經(jīng)典體系的嬗變和定型,其成功經(jīng)驗(yàn)和學(xué)術(shù)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們編好《儒藏》的精神食糧。
早在上古時期,這里便誕生了為儒、道、墨三家共同推崇的“生于石紐”(《孟子》佚文)、“興于西羌”(《史記·六國年表》)的大禹,《尚書》載其因治水需要而悟“九疇”,于是衍為《洪范》(見《尚書》);又因伏羲氏《河圖》,于是演為“三易”之首的《連山》(《山海經(jīng)》佚文),兩書及其所含“陰陽”觀念和“五行”學(xué)說,奠定了后世中國(特別是儒家)經(jīng)典文獻(xiàn)的基本形態(tài)和中國哲學(xué)的基本范疇。至于孔子所贊大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的孝道觀念,以及《考工記》所載“夏后氏世室”的宗廟制度,更是后世儒家堅(jiān)決持守的道德倫理和禮儀基礎(chǔ)。約當(dāng)殷商時期的“三星堆”遺址,所出土青銅祭壇,明顯表現(xiàn)出“三界”(天、地、人)合一的信仰體系。戰(zhàn)國時成書的《世本》又揭示蜀為“人皇之后”(《華陽國志》則稱蜀“肇于人皇”之際),天皇、地皇、人皇三才一統(tǒng)的觀念,又與三星堆出土青銅器吻合起來。《華陽國志》記載蜀王亡故,不同中原之謚號,而以“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命其廟號,又與《洪范》中所載五行相生相克的觀念結(jié)合起來。至于禹所娶涂山氏之婢女吟唱“候人兮猗”的《南音》,后為周公、召公所取法“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又為屈原所依仿,造為楚辭(謝無量《蜀學(xué)會敘》)。所有這些,均可視為早期巴蜀學(xué)人對儒學(xué)經(jīng)典文獻(xiàn)形成的特別貢獻(xiàn)。
秦漢時期,物華天寶的巴蜀地區(qū)不僅是祖國統(tǒng)一的堅(jiān)強(qiáng)基地,也是中華學(xué)術(shù)孕育和發(fā)展的搖籃。漢景帝末年,廬江舒城人文翁為蜀守,有感于秦后天下絕學(xué),乃修起學(xué)宮于成都市中,派張寬等18人前往長安從博士講習(xí)孔子“七經(jīng)”(在中央所傳《詩》《書》《易》《禮》《春秋》之外另加《論語》《孝經(jīng)》),張寬等學(xué)成歸來,即居學(xué)宮教授;文翁復(fù)選下縣弟子入石室肄業(yè),成功改變巴蜀的“蠻夷風(fēng)”,實(shí)現(xiàn)移風(fēng)易俗,儒學(xué)正式扎根巴蜀。巴蜀士子,或負(fù)笈萬里,求學(xué)京師,或居鄉(xiāng)開館,傳道授徒,形成頗具特色的“蜀學(xué)”流派,史書或稱“蜀地學(xué)于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循吏傳》),或直接說“蜀學(xué)比于齊魯”(《三國志·蜀書》《華陽國志》)。巴蜀士子以經(jīng)學(xué)為學(xué)習(xí)和追跡對象,在儒家故里之外又形成一個儒化地區(qū),故當(dāng)時巴蜀有“西南鄒魯”“岷峨洙泗”之稱。文翁石室是漢朝首個由地方政府建設(shè)的高等學(xué)府,在歷史上成績卓著,影響深遠(yuǎn),史稱“后有王褒、嚴(yán)遵、揚(yáng)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書·地理志》)。漢武帝推廣其經(jīng)驗(yàn),“令天下皆置學(xué)校官”(同上),于是漢代遍開郡國之學(xué),中國進(jìn)入全面“儒化”時代。當(dāng)時漢博士所守經(jīng)典為《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蜀中所傳則是“七經(jīng)”,在“五經(jīng)”外增加《論語》《孝經(jīng)》,形成“蜀學(xué)”重視倫理教化的經(jīng)典特色。“七經(jīng)”概念在東漢得到普遍認(rèn)同,儒經(jīng)體系于此實(shí)現(xiàn)從“五經(jīng)”(重史)向“七經(jīng)”(重傳記)的轉(zhuǎn)型。
東漢末年,天下紛亂,中央太學(xué),徒具故事。然而時鎮(zhèn)巴蜀的河間人高卻在成都大興文教,既恢復(fù)被戰(zhàn)亂所毀的文翁石室,又在石室之東新建祭祀周公、孔子等歷代圣賢的“周公禮殿”,教育與祭祀并重,形成中國學(xué)校“廟學(xué)合一”“知信合一”的體制,這比北魏在都城洛陽實(shí)行的同一制度提前300年!
唐自武后,濫用威權(quán),學(xué)官多授親信,太學(xué)形同虛設(shè),但是遠(yuǎn)在西南的巴蜀地區(qū),卻社會穩(wěn)定,人文輻輳。八世紀(jì),成都誕生了以“西川印子”命名的雕版印刷物,肇開人類印刷術(shù)之先河,宋人有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朱翌《猗覺寮雜記》)五代時期,巴蜀圖書出版成績卓著,后蜀宰相毋昭裔于廣政元年(938)倡刻《石室十三經(jīng)》,歷180余年至北宋宣和五年(1123),最后一經(jīng)《孟子》入刻。蜀石經(jīng)有經(jīng)有注,規(guī)模宏大,“碑越千數(shù)”(晁公武說),堪稱中國“石經(jīng)”之最。蜀石經(jīng)可貴之處,是在唐代盛行的“九經(jīng)”(《易》《書》《詩》“三禮”“三傳”)體系(即使《開成石經(jīng)》刻了十二部,也只稱《石壁九經(jīng)》)外,增加《論語》《孝經(jīng)》《爾雅》和《孟子》,以《石室十三經(jīng)》(或《蜀刻十三經(jīng)》)命名(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曾宏父《石刻鋪敘》),正式形成“十三經(jīng)”體系。這套刻在石頭上的經(jīng)書,促成了儒家《十三經(jīng)》的最后形成。毋氏還將原來用于“陰陽雜書”和佛家讀本的雕版技術(shù),移刻儒家經(jīng)典以及《文選》、類書等正規(guī)文獻(xiàn),為五代、北宋儒經(jīng)“監(jiān)本”等權(quán)威刻本樹立了榜樣。
宋代“四川”刻書業(yè)十分發(fā)達(dá),“蜀版”是當(dāng)時學(xué)人和藏家努力羅致和收藏的珍品,楊慎有“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丹鉛續(xù)錄》卷六)之說;開寶年間由政府主刻的多達(dá)13萬片的“開寶大藏經(jīng)”,即由高品張從信督刊于成都,成為后世藏經(jīng)鼻祖。南宋理宗時,蜀人魏了翁將唐孔穎達(dá)、賈公彥等《九經(jīng)注疏》刪節(jié)為《九經(jīng)要義》,以便學(xué)人。
明代,曾為四川右參政、按察使的曹學(xué)佺,既纂輯巴蜀掌故資料成《蜀中廣記》108卷,又感于“二氏有藏,吾儒何獨(dú)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余年,功未及竣”(《明史》本傳)。清乾隆中,在周永年重倡“儒藏說”的同時,四川羅江人李調(diào)元獨(dú)自輯刻《函海》,收書150余種,許多稀見的儒學(xué)著作得以保存。晚清經(jīng)學(xué)殿軍廖平嚴(yán)分經(jīng)史,善說古今,發(fā)凡起例,撰《群經(jīng)凡例》,欲以今古文學(xué)為標(biāo)準(zhǔn),撰著《十八經(jīng)注疏》,以糾正東漢以下注疏今古無別、學(xué)派不清(如《十三經(jīng)注疏》)的狀況。近代,曾任四川存古學(xué)堂督監(jiān)(院正)的蜀中才子謝無量,曾倡議編刻《蜀藏》;辛亥遺老胡淦諸人,又計(jì)劃編纂“四川叢書”,只可惜皆因時勢不濟(jì)而未成。
歷史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在近代“蜀學(xué)”發(fā)祥地的四川大學(xué),再度提出了儒學(xué)文獻(xiàn)整理和體系重建的問題,那就是《儒藏》編纂。承擔(dān)《儒藏》編纂的四川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自1983年成立以來,上繼文翁石室“七經(jīng)”教育之遺澤,下承蜀刻“十三經(jīng)”、廖平“十八經(jīng)”之余緒,在前輩學(xué)人組織完成《漢語大字典》《全宋文》等大型辭書和總集之后,又于1997年發(fā)起了“儒學(xué)文獻(xiàn)調(diào)查整理和《中華儒藏》編纂”工程。針對當(dāng)時中國文化品牌常常被域外國家搶注的現(xiàn)象,為保護(hù)儒學(xué)知識產(chǎn)權(quán),川大學(xué)人特向國家商標(biāo)總局申請“儒藏”商標(biāo)注冊,向四川省新聞出版局申請《儒藏》著作權(quán)登記。
編纂《儒藏》,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編好。雖然歷代學(xué)人都有儒學(xué)文獻(xiàn)整理的實(shí)踐,如唐修《九經(jīng)正義》、宋刊《十三經(jīng)注疏》、明纂《四書五經(jīng)大全》、清成《通志堂經(jīng)解》和《皇清經(jīng)解》(正續(xù)編),但卻沒有總匯儒學(xué)各類文獻(xiàn)而成《儒藏》的先例。明朝萬歷中后期,孫羽侯、曹學(xué)佺曾先后提出《儒藏》編纂設(shè)想,卻無具體編纂方案;清周永年、劉因等再倡“儒藏說”,也沒有留下相應(yīng)成果,其經(jīng)驗(yàn)和體例都無從參考。
為取得《儒藏》編纂的學(xué)術(shù)支撐,川大學(xué)人申請了教育部重點(diǎn)研究基地山東大學(xué)易學(xué)與中國哲學(xué)研究中心的重大項(xiàng)目“儒家文獻(xiàn)學(xué)研究”,對儒學(xué)文獻(xiàn)源流和演變軌跡、文獻(xiàn)類型、重要典籍進(jìn)行系統(tǒng)探索,撰成240余萬字的《儒藏文獻(xiàn)通論》,為《儒藏》編纂做足前期學(xué)術(shù)儲備。同時,針對中國儒學(xué)大師輩出、流派眾多的歷史,為摸清儒家學(xué)人的師傳授受、學(xué)術(shù)陣營和學(xué)派特征等情況,我們還聯(lián)合港臺學(xué)人組織實(shí)施了“歷代學(xué)案”整理和補(bǔ)編工作。該項(xiàng)目對前人所編五種學(xué)案(唐晏《兩漢三國學(xué)案》、黃宗羲《宋元學(xué)案》、王梓材等《宋元學(xué)案補(bǔ)遺》、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徐世昌《清儒學(xué)案》)重新進(jìn)行校勘,對前人未編的時段進(jìn)行補(bǔ)編(《周秦學(xué)案》《魏晉學(xué)案》《南朝學(xué)案》《北朝學(xué)案》《隋唐五代學(xué)案》),共形成《中國儒學(xué)通案》十種,形成脈絡(luò)貫通、傳記齊全的全景式“儒學(xué)流派通史”。
有了對儒學(xué)文獻(xiàn)的總體了解和儒學(xué)發(fā)展史的脈絡(luò)把握,就大致具備了從事《儒藏》編纂所需的文獻(xiàn)學(xué)知識和學(xué)術(shù)史背景。再參考《道藏》“三洞四輔十二類”、《大藏經(jīng)》的“經(jīng)律論”等方法,初步將《儒藏》按“經(jīng)、論、史”三大類區(qū)分:《經(jīng)藏》收錄儒學(xué)經(jīng)典及其為經(jīng)典所作的各種注解、訓(xùn)釋著作,包括元典、周易、尚書、詩經(jīng)、三禮、春秋、孝經(jīng)、四書、爾雅、群經(jīng)、讖緯等11目;《論藏》收錄儒學(xué)理論性著作,包括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等5目;《史藏》收錄儒學(xué)史料著作,包括孔孟、學(xué)案、碑傳、史傳、年譜、別史、禮樂、雜史等8目。共計(jì)“三藏二十四目”。這樣專題清晰,類屬明備,既照顧到儒學(xué)文獻(xiàn)的歷史實(shí)際,也方便當(dāng)代學(xué)人的翻檢和閱讀。
鑒于二十世紀(jì)以來人們對儒學(xué)歷史存在隔膜,也為了給學(xué)界提供儒學(xué)史研究的系統(tǒng)資料,川大《儒藏》首先啟動了“史部”編纂。自2005年出版首批《孔孟史志》(13冊)、《歷代學(xué)案》(23冊)、《儒林碑傳》(14冊)以來,陸續(xù)于2007年、2009年、2010年、2014年,分四次出版了《年譜》《史傳》《學(xué)校》《禮樂》《雜史》等類,至2015年年初,《儒藏》史部274冊已全部出齊,實(shí)現(xiàn)了2500余年儒學(xué)史料的首次結(jié)集。其后又于2016年、2017年,出版“經(jīng)部”86冊;全套650冊,將于2018年出齊。
在編纂體例上,本著“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理念,我們試圖將入選《儒藏》的書籍,按一定體例編錄,使其更具系統(tǒng)性,遵從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清《四庫全書總目》的傳統(tǒng),于《儒藏》開篇設(shè)《總序》一篇,三藏各立《分序》,小類各設(shè)《小序》,每書前又加《提要》。試圖通過這些敘錄的介紹和勾連,將各自成書的儒學(xué)文獻(xiàn)聯(lián)系在一個統(tǒng)一的框架和完整的體系下,使《儒藏》成為“用文獻(xiàn)構(gòu)建的儒學(xué)大廈”。
千年儒學(xué),百年滄桑。面對儒學(xué)不振、花果飄零、文獻(xiàn)殘破、學(xué)科無歸的狀況,重新回顧蜀學(xué)先賢從事儒學(xué)文獻(xiàn)研究的學(xué)術(shù)實(shí)踐,對我們研究和重審儒學(xué)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以系統(tǒng)體例編纂《儒藏》,不僅有利于儒學(xué)成果保存推廣,而且有利于儒學(xué)學(xué)科重建、儒學(xué)價值重估,特別是儒家學(xué)術(shù)的再創(chuàng)造和再發(fā)展。以儒學(xué)為本位、以文獻(xiàn)為載體,以“三藏二十四目”為紐帶,通過重新構(gòu)建儒家文獻(xiàn)體系,達(dá)到恢復(fù)儒學(xué)大廈的效果,從而找回儒學(xué)文獻(xiàn)的經(jīng)典地位和學(xué)術(shù)價值,必將為儒學(xué)的當(dāng)代傳承和發(fā)展找到突破口。